染色馒头、牛肉膏、瘦肉精、工业胶果冻、三聚氰胺奶粉、毒豆芽,毒生姜, “毒血旺”……,2011年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次次地考问着国人的道德底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果说物质生活无比丰富的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那唯独“缺心眼”、“缺德”。有人说,当今社会什么都在发展进步,唯独人的道德品质没有进步。这些话听起来有点逆耳,却证明了胡锦涛总书记“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的道德教育指示的必要性、迫切性。人一旦丢掉了诚信,人性就显得可恶、可怕、可耻。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败坏,良心迷失,缺乏诚信的社会里,这不仅是悲哀,更是悲剧。今天有必要重拾“诚信”之道,建立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相匹配的诚信机制。
一、延陵季子——中华民族诚信第一人
说到诚信不得不提到我们常州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诚信第一人,延陵季子。季札以自己的道德践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三让王位、徐墓挂剑、礼乐教化、延陵归耕、大义救陈等言行载于正史,为历代名家所称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特别是让国体现的谦让、挂剑体现的诚信在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一般意义上,“诚”即诚实诚恳,主要指主体真诚的内在道德品质;“信”即信用信任,主要指主体“内诚”的外化。“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而这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道德典范莫过于2500年前的季子。春秋时期吴王余祭四年春天。季札奉命出使鲁国,接着又访问郑国、卫国、晋国。途中,路过徐国,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招待。季札带宝剑经过徐国,徐国的国君看到这口宝剑,他嘴上虽然没说,可脸上的表情却显示着很想得到这口剑。季札因为还要佩戴宝剑出使中原各国,所以没将宝剑献给徐君,但心里已经决定,回程时一定将宝剑献给徐君。当年秋天出使各国后,季札又路过徐国,而徐君已经去世,埋葬在徐国都城的郊外。可是,季札还是要解下宝剑赠给徐国的嗣君。随从急忙劝阻:“此剑乃吴国之宝,不可以赠人。”季札回答说:“当日路过,徐君观剑,口虽不言,脸上的表情却显示着爱剑之意。那时,我已决定回来再献。如今他故去了,我不献剑,即是欺骗自己,为一口剑而自欺,正直的人不为。”于是季札把剑挂在徐君墓地的树上,行礼之后,便踏上归国之路。“季子挂剑”即成为“诚信”的一个标志,被百代文人广泛引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华民族独特而丰富的诚信观
常州以古代延陵季子,近现代恽代英、冯仲云三大诚信典范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丰富的诚信观。“诚”与“信”一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其基本含义是指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在基本字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具特色并具有丰富内涵的诚信观。
诚信是立人之本
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认为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诚信是齐家之道
唐代著名大臣魏徵说:“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间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就能和睦相处,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诚信、互不信任,家庭便会逐渐四分五裂。
诚信是交友之基
只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才能达到”朋友信之”、推心置腹、无私帮助的目的。否则,朋友之间充满虚伪、欺骗,就绝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
诚信是为政之法
《左传》云:“信,国之宝也。”指出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法宝。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宁肯去“兵”、 “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因为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统治者,国家朝政根本立不住脚。因此,统治者必须“取信于民”,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诚信是经商之魂
做生意不可失去信用。 俗话说“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 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企业家,红顶商人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虽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廉贾经商,取利守义。
诚信是心灵良“药”
古语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只有做到真诚无伪,才可使内心无愧,坦然宁静,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是人们安慰心灵的良药。
综观而言,诚信对于自我修养、齐家、交友、营商以至为政,都离不开“信”。“信”成为封建社会“五常”之一,与仁、义、礼、智,共同构建了封建社会的五条道德标准。可见诚信在古代和现代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重建诚信是当今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国信任危机的历史渊源
尽管“信”在古代被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但在二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诚信机制。传统社会是农耕经济,农耕经济聚族而居的特点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简单,若是犯了错,18代祖宗都能给翻出来,用现在时下的话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使人不能不讲诚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社会的农耕经济发展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原来建立在家族、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内的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的“诚信”,因血缘淡化,地缘被打破,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被打破。传统社会政治层面的“信任”和经济层面的“信用”也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问题重重。由于皇权是唯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发育成熟,并覆盖全社会。而家族皇权也因为缺乏资源和能力,无法通过有效提供公共品,建立起国家和社会间的信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皇权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进一步使社会产生对社会信任生成不利的机制。
当今社会主要的信任危机
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1、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虽然并不需要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例如:商品房价居高不下,安居工程的资金短缺使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心。
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2、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入手来解析。
许多欺诈和其他非法牟利的猖獗,其实正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造成的。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
监管缺位的逻辑也差不多。不同于西方社会依靠社会组织、司法体系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分工模式,中国的监管权主要分散地“集中”在政府的一个或几个功能部门。在“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这些监管部门在“增加管理收入”和“消弭一切不法”之间作何选择是很明显的。更何况,追查到底可能损害其他平行部门的利益,涉及不菲的行政成本甚至政治风险。当监管本身变成一种垄断的利益来源,那么,“监督不给力”和问题“越查越多”的结果也就是可想而知的。
3、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当代的社会转型,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西方工业化后由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对信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式微,但却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 ,天津“许云鹤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可怕的是讲诚信就是去“送死”,讲诚信就得吃亏上当,就在我们常州也发生八旬老太摔倒在地,好心人把她搀起,却因此惹出了麻烦的事。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
重建社会诚信是当今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如何重建诚信呢?
如何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当代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
在思想道德领域要加强道德教化。这里不得不提到教育的力量。人不是天生就成为了人应成为的样子,没有道德教化人与大猩猩没有本质的区别。道德教化是能把人从人的本性状态提升到人性状态的工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多家媒体报道的“诚信夫妇”马保杰夫妇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诚信做人”课。“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了这一朴素道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靠捡垃圾,打短工,守厕所,用13年辛苦还钱诠释着“诚信做人”的美德。“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 2009年底哥哥孙水林为赶在年前给农民工结清工钱,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兄弟俩20年来坚守的的“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的诚信之举深深地打动了全中国的人。更有用生命捍卫职业操守的司机吴斌。当被高速公路上飞驰而来的异物砸中后,他沉着冷静最大程度地保护了34位旅客的生命安全而他却倒下了,这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职业操守,促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如果我们的官员能内诚于心,外信于人,我们的商人能内诚于心,外信于人,我们的百姓能内诚于心,外信于人,我们的行业能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中国将是乐土。
四、传承季子文化,建设诚信常州
季子,姬姓,吴氏,名札。号公子札、吴札、吴季子、延陵季子。生于公元前576年(周简王十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卒于公元前485年(周敬王三十五年、吴王夫差十一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公元前547年封邑延陵。晚年躬耕于武进焦溪舜过山。2500余年来,季札后裔繁衍于全国各地及数十个国家。在古区域的延陵常州武进、江阴、丹阳以及苏州、宜兴和山东、安徽有近20处“季子祠”、“季子庙”等纪念场所,延陵邑人世世代代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缅怀延陵人文始祖、“中华民族诚信第一人”季札,纪念与孔子齐名的先圣(有北孔南季之说)。季子的大圣大贤、大诚大信、大智大德,已成为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道德史、外交史的重要来源。季札虽是2500年前的人,但其思想、理念、道德情操无不与当今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根,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旨一脉相承。我们今天传承季子文化,就是要建设诚信常州。为此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把延陵季子列为常州首名先贤,作为常州人的诚信典范、道德楷模。要像宣传孔子那样去宣传季子的思想。在2013年的花博会上,以季子为常州标识性形象。建议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季子生日)作为常州纪念延陵季子的诚信节,使“中华民族诚信第一人”季札的躬耕地常州成为“当今中国诚信第一城”。
二是建议修复、建设延陵季子纪念场所,发展以诚信教育为重点的文化旅游业。如将人民公园改为季子公园;恢复历史上的嘉泽季子庙,扩建成中国延陵季子文化园,并建季子碑林,为2013年花博会增添人文光彩;塑全国最大最高的季子雕像或铜像,立于淹城或新天地公园、市民广场,作为其封邑延陵的标志性场景;在武进郑陆镇境内延陵舜过山建季子森林公园,并和附近江阴申港镇的季子庙连接,形成新的旅游景点。
三是建议常州市政府和武进区政府,在财力上支持以吴镕为筹备组长的筹建中华延陵季子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华延陵季子网站,使常州真正成为海内外研究季札文化的服务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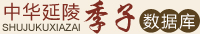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32041202002256
苏公网安备32041202002256